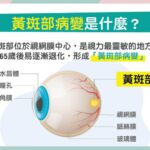“讀+走→寫”:我的治學方程式——在上海大學榮休儀式上的發言 鄧偉志 |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榮休教授
本文系鄧偉志教授榮休儀式發言稿
文中圖片由鄧偉志教授本人提供
鄧偉志教授
回顧我這80年,殊覺慚愧。我多次寫文章講“有付出方有傑出”,可我自己有付出而沒有傑出,是個無能的例外。我寫了一千多萬字(不包括主編的),出版了文集24卷,還有幾百萬字尚待出版。遺憾的是,我的作品有數量而無質量。近40年,隨着國家改革的步伐有所進步。改革讓學者改觀,開放讓學者開朗、開竅、開通。如果一定要我把我的80年的歷程作個概括的話,只有三個字:讀、走、寫。
讀
先說讀。學問是積累起來的。要把學問做好,必須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。這就要讀書。有句名言說得
好:讀書就是站在前人、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。我讀書是很積極的,夙興夜寐,披星戴月地讀。在不宜讀書的車上、飛機上讀。1960年冬天下鄉,不便在農民家裡讀,我跑到幾個坆墓中間,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讀。我相信“開卷有益”,開的卷越多越有益。見賢思齊,我崇敬中國乃至世界有名著的名人,我需要從他們的書中吸取營養。我腦子有很多疑問,促使我從同行的專業書本上找到他們的闡釋。見到書上有用的,我就抄卡片(類似電腦下載),如今還保存着一抽屜卡片。我嗜書如命,有24個書架,放着亂七八糟的書,大部分是文科書,也有理科的書。我喜歡借書,我有北京、上海好幾家圖書館的借書證。沒借書證的圖書館,我請朋友代借。我讀好書,也讀叛徒、漢奸寫的壞書,讀被各國視為反面人物的書。讀這些人的書,主要是作為放矢之“的”,有的也可以彌補好書“為尊者諱”的缺陷。好人不忍說“尊者”做過的錯事,可是壞人是不給“尊者”留面子的。“智者千慮,必有一失;愚者千慮,必有一得。”很多名人的正史、野史、艷史,以及少數人的醜史,我或多或少能說出幾句。書讀得越多,疑問越多,也就越是能夠做到對任何國家的學術權威尊重而不迷信。人無完人。古人“說大人則藐之”似乎有點過分,認為任何大人都有可“藐”之處則不為過分。很多學者晚年的觀點跟早期不一樣。不一樣又分兩類,一類是前進,晚年糾正早年的錯誤;一類是倒退,晚年不如早年。這都要求我們冷靜分析,不要“揀到籃子里都是菜”,不要抓住一點,不及其餘。只有前後左右都看過,多維度會帶來理論的深度、高度,才能接近真理。請注意“接近”二字。真理是過程,是進行式。學問做得再好,也不可能窮盡真理。“學然後知不足”,越是讀書多的人,越是有學問的人,越能做到虛懷若谷;越是虛懷若谷,越喜歡繼續多讀書。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的人容易自滿,自負。

說起與書的關係,我還有三個特殊經歷:
一是吃住在圖書館。孤本、珍本書不許出館,只能在館裡看。我們任務緊迫,怎麼辦?圖書館同意我們住在圖書館裡,書不出館,夜以繼日地在館裡看書。既不違規,也保障了進度。我與另外兩位學者在靠近黃陂路的一排房子里的一間寬2米,長10多米的怪房間住了一個多月,每天晚上23時以後到上圖對面的五味齋飯店吃一碗麵條,可以報銷二毛五分錢。
再一個特殊經歷是印過書。上海曾有一家設備最先進的印刷廠叫海峰印刷廠,很多人不知道,因為不在上海,在安徽績溪縣的眼睛山上,內部稱那裡為“小三線”。當時考慮,一旦打起仗來,上海不能印報紙,就到眼睛山上印。“文革”後恢復高考,考卷就在海峰廠印製。那裡的字模最佳,獲過獎,印出來的文字,看起來不吃力。我在海峰廠撿過鉛字,拼過版面,笨手笨腳,速度不及排字工人的1/10,深感出書之艱難,深感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應當結合。
第三個特殊經歷是賣過書:我在多家新華書店當過賣書的“營業員”。“文革”前,幹部每星期四上午必須參加勞動。我是書痴,參加什麼勞動?經領導同意,我到書店站櫃檯,在上海福州路、衡山路、淮海路、瑞金路的大書店賣書。賣書有個好處,顧客來買時,可以跟他們聊兩句:“給誰買的?”“怎麼喜歡這本書?”“為什麼不買哪本書?”顧客是上帝。“上帝”的回話比答問卷更真實。由於大書店分類分得細,站櫃檯只能了解一類書,有局限性。我還到淮海路、華亭路口的一家小新華書店賣過書。在小書店可以了解讀者對各類書的看法,搞點比較研究。所有這些對自己如何寫書都有所啟迪。書是給讀者看的。讀者是書的評委。作者得聽讀者的。賣弄文字,自我陶醉,如果讀者不喜歡就是敗筆。
讀書是苦差事,也是享受。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里寫道:“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,必經過三種之境界:‘昨夜西風凋碧樹,獨上高樓,望盡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帶漸寬終不悔,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眾里尋他千百度,驀然回首,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一旦進入第三境,從書中找到燈火闌珊處的“那人”,悟出了真諦,會拍案叫絕,欣喜若狂。
書本里的知識是實踐的反映,是從實踐中提煉出來的,還要回過頭來接受實踐的檢驗。因此,要做好學問,要有所創新,要有真知碩見,還必須走進實踐。下面講“走”。
走
走,不是走馬觀花,不可霧裡看花,要下馬觀花,下馬栽花。走,主要不是走紅地毯,要走曲折坎坷的山路和田間小道。我有次坐長途汽車,半路下雨,從車頂滲水滴在旅客頭上。旅客哇哇叫。司機說:“對不起,我馬上修好。”司機到田地里抓把紅色的爛泥,搓搓揉揉,爬在車頂上把粘泥往縫裡一塞,便不漏了。

我的走,是走又不是走,常常是摸、爬、滾、打。
摸,我不是摸着石頭過河,我是摸着繩子過河。為了考察滇東南的少數民族,必須經過橫斷山脈,一道高山,一道急流,急流水深到胸口,但坡度大,衝力大,一不小心就會“去見胡伯伯”(衝到越南之意)。在兩岸之間拉根長長的繩子,我們立於繩子上游,緊緊抓住繩子往前走,大浪撲來,有繩子擋住,從而平安越過急流。這是一種“摸”,還有一種摸,是摸着鐵索橋過深谷。鐵索橋由四條鐵鏈組成,上面兩條是供手抓的,下面兩條是供腳踏的,中間沒有橫板。當地人走鐵索橋很快,也可以兩三人同時走。我們不行,只能一個人慢悠慢悠地過鐵索橋,因為自己的腳力自己知道。如果兩人走,用力不均,一腳蹬空,粉身碎骨。
爬,為了進廣西柳城縣的巨猿洞,必須爬山南一塊筆直的30米高的大石頭。為了節省時間,僮族兄弟一大早先從北坡艱難地爬上去,然後由他們立於洞口,向南面放一根粗繩是供我們抓住向上爬的,再放一根細繩讓我扎在腋下和胸口,既是作保險用的,也是用來拉着我們向上爬的。爬了一二十分鐘,見到了在向人類進化過程中半路消亡、被稱為人類“叔父”的巨猿化石。還有一次,為了見苦聰兄弟,要過一面長百米,坡度70度的山坡。說是山坡,只有碎石,沒有巨石;沒有巨石,卻不能長灌木;沒有灌木,就沒有抓手,只能四腳着地往上爬。人是由爬行動物變出來的,可是再回到爬行,卻比用兩腿走更吃力。當我們爬上來大喘了幾分鐘以後,陪同我們的紅河州宣傳部同志講了個故事。他有次陪雲南日報總編爬上來以後,總編說:“以後你們來稿,我們再不批示‘補充材料’了。現在知道要你們補充,就是逼你們爬行。”
滾,不是走的必須,但是走的難免。有次為了到雲南的麻栗坡看化石,在哀牢山裡騎馬爬山,馬太累了,馬失前蹄,我從馬頭上滾進了山谷。在往下滾的時候,我想完了,幾萬年、幾億年以後自己就變成化石供後人研究了。沒想到滾了十來米,被一棵小樹擋住。我慢慢抓住荊棘爬了上來。當時不覺痛,上來一看雙手被刺兒刺得全是鮮血。好在刺兒小,流血不是泉涌。
打,走路怎麼會打起來呢?會打,不打不行。有次我們穿過麻瘋病區以後,要穿過密林。密林里充滿荊棘,馬不肯走。馬不走,人不能不走。我們穿着帆布靴,帶着蛇葯,以防蛇咬。想不到樹上的螞蟥(水蛭)會掉進脖子里。誰都知道,螞蟥是在水裡的,哪知那裡在雨季螞蟥會上樹,因此碰到樹枝時,螞蟥會掉在脖子里吸血,而自己卻感覺不出。這就要求我們每走一段路,便要找片空地,把衣服脫下,互相看看有沒有螞蟥在吸血。有,就一巴掌打過去,螞蟥便會掉下來。有一個螞蟥打一巴掌,有兩個螞蟥打兩巴掌,不打螞蟥會吸血不停。打,不止一次,穿密林需要一個多小時,彼此要停下來打上五六次。——我過去寫文章很喜歡用“披荊斬棘”這個成語,真要披荊斬棘時,方知過去寫“披荊斬棘”四字時是何等的輕飄飄,沒分量!“事非經過不知難。”我在密林里下決心:今後一定要以今日之“披荊斬棘”的精神在求學之道上“披荊斬棘”。
走,絕不會白走。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?”我深感“不入前人洞穴,焉知人之初的本性?”在紅河州我們與金平縣的苦聰人相處過好幾天。他們的歌聲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:“我們沒有吃過一粒米,我們沒有穿過一件衣,我們沒有牽過一頭牛。天上陰森森,地上濕淋淋……”他們在1953年以前,處於原始社會解體階段。現在有人要打貿易戰。苦聰人搞的是“無聲貿易”,把虎皮、籐編放在十字路口,兄弟民族可以用一把鹽、一隻破鐵鍋換張虎皮。不等價交換沒問題,假如拿走虎皮,什麼都不留下,那一定是一命嗚呼。他們用的工具是弩,不是箭,一弩射過去,白拿他們東西的人必死無疑。把弩拉開要費很大勁。為我們當翻譯的拉祜族兄弟只有四五十歲。他見苦聰人氏族長手裡的弩很感興趣,拉了幾次拉不動。苦聰人的氏族長年過七旬,接過來一拉就拉開了。中年人沒老年人力氣大。苦聰人搞平均主義,“有飯大家吃,沒飯大家餓”。自己採到3個,見對方采了5個,不用提醒,對方會自然地、自覺地給自己一個。1953年前苦聰人是磨擦取火。磨擦取火有三種,苦聰人採用的是最落後的一種,要花大半天時間。因此,對他們來說,下雨時保存火種是頭等大事。怎麼保存火種?只能用類似女排獲勝時人疊人的那種方式,用身體擋住雨水。人疊人最下面的人是誰?是氏族長。70多歲的氏族長打開胸部、腹部給我們看,全是傷疤連傷疤,傷疤摞傷疤。氏族長這般吃苦在前的崇高品德,多麼值得今天帶“長”字號的人學習啊!
走就是調查,是真正的田野調查法。邊走邊看、邊問、邊聽,要像中醫一樣,望、聞、問、切。學問是問出來的。一問一答,會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快感。問,有時需要明知故問,要反覆問。不要對自己的所“知”過於自信,明知故問是核實,是檢驗。
2018年4月我去了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玻利維亞。那裡過去是西班牙殖民地,可是殖民者沒有上過4500米以上,因為上到那裡,人就變成“人干”。我想上去。《國際歌》唱道:“起來,全世界受苦的人……”如果不了解全世界受苦的人,如何解救全世界受苦的人?國際歌是唱的,更應當是乾的。學以致用,學者不僅要解釋世界,更要改造世界,至少要開出改造世界的藥方,提出社會發展的途徑。在玻利維亞,去海拔4500米必須走一條“危險之路”,去海拔5000米必須走一條“死亡之路”。我上到了4500米,在危險之路上,出了洋相,喘不過氣來,步履維艱。我估計會死亡,便邁一步說個“死”字,再拔出腿來邁一步說個“活”字,“死——活——死——活”地往上爬。哪知同行的人聽了說我嘴裡喊的是“世——哈——”,因為發“死——活”的聲音要用力氣,我已沒那個力氣了,所以同行的人無論如何不讓我再上“死亡之路”。我們只好把生活在5000米的印加人請下來介紹情況。可以說,他們衣食住行用、生長老病死的情況,全是我做夢也想象不到的,全是書本上沒見過的。五千米寒冷,印加人怎麼禦寒?他們是在床下養幾十隻荷蘭兔,用荷蘭兔的體溫來提高室溫。他們做菜沒佐料,用小便晒乾後的白鹼當佐料。他們洗手沒肥皂,還是用上面所說的小便晒乾後的白鹼當肥皂。西班牙後裔和印加人都承認一句話:“生活在五千米的印加人在活着的時候是不生病的。”意思是:有病當沒病。有個國家的土豆(馬鈴薯)專家,辦了個土豆博物館,展出了兩三千種不同的土豆,認為很全了。想不到他看了印加人高海拔、高紫外線照射下的土豆驚嘆了,怎麼會有如此鮮紅的土豆?怎麼會有辣如椒的土豆?怎麼還有甜如蘋果的土豆?他認輸了,我也認輸了。
山外有山樓外樓,天下學問永不休。“世事洞明皆學問,人情練達即文章。”學問就在自己腳下,只要是有心人,走到哪裡都能發現學問。全國56個民族我訪過四十多個。台灣布農族酋長的禮服是珍珠衣。布農兄弟說:“現在沒有了珍珠衣,很抱歉無法供你們欣賞了。”他們說的時候,頗有傷感。我告訴他們,我的老師1947年在台灣研究民族問題時,買過一件珍珠衣,現在復旦大學博物館。他們聽了立即興奮地拉着我跳舞。後來布農族到貴州與布衣族開研討會。他們認為布農與布衣是一家親。科學無國界。全世界190多個國家,我去過60來個,絕大部分是自費去的。把錢用在哪裡,都不如用在調研上。古人說: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。”我是捧着一顆求學的心走進五大洲的。我與162個國家的人握過手,聊過天。我將出版一本三百頁的《與百國百姓在一起》。寫得很淺薄,稱不上國別比較研究。外事無小事,我側重於講民俗,不為國家添麻煩。讀和走,對做學問的來講不是終極目標。學者的目標是把所讀的、所走的化合成書。下面講一講我是如何寫的。
寫
我寫文章成癮。我這個人不吸煙,沒煙癮;不喝酒,沒酒癮。但我寫文章成癮。畫家石濤的“搜盡奇峰打草稿”,我見過複製品。說“搜盡奇峰”是從寫實角度講的,很有道理。不過,我常常是一見“奇峰”就寫,不等捜盡奇峰就寫。盡不儘是相比較而言。我相信石濤在三四百年前那種情況下,他既沒捜過阿爾卑斯山的勃朗峰,也沒搜過安第斯山的阿空加瓜峰,恐怕連珠穆朗瑪峰也沒去搜過,不排斥他的聚峰一幅能流傳百世。我這個人不怕淺,我主張循序漸進,由淺入深,深入淺出。我這個人不怕失敗,不怕出錯,錯了就改。對勇於改正錯誤的人來講,“錯誤是正確的先導”。有些大學者出集子時抹掉過去的錯誤文字,冒充一貫正確,欠妥!更沒法說出口的是,我這小人物是受他們大人物文章中錯話的影響而跟着錯的,如今他們文章中沒有了錯話,那我們小人物是怎麼錯的?難道只有內因沒有外因嗎?1957年之前的大學十分提倡“獨立思考”。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,留在上海社科院學習室,導師教導我們一要直寫胸臆,二要筆不離手。這八個字讓我終生受用。導師說這話時電腦還沒出現,現在有電腦了,網絡化了,我這個時代的落伍者是用漢王筆上網的,漢王筆還是筆,沒辜負導師教導。
一個人在與人相處時,要求同存異。在學術研究中,要求異存同。拾人牙慧是沒出息的表現。愛重複套話,是“高級”抄襲,沒有半點創新,讀了味如嚼蠟。說得重一點,套話連篇,對上是“語言行賄”,對己是“語言索獎”。幾十年來我在寫作上求異求新,追求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。後來知道理論上的革故鼎新之路不平坦。革故,“故”會出來罵;“求異”會被人視為“異類”。我得罪過好幾位大權威,包括曾經喜歡我的權威。說是“真理面前,人人平等”,實際上各國都存在“人微言輕”的問題。寫作之路比我前面說的爬哀牢山還曲折。
我知難而進,寫過幾篇不合時宜的文章。在黨史研究中出現不太尊重歷史的問題時,我著文羅列了黨史研究中的十種現象,批評“一俊遮百丑”“一丑遮百俊”,批評“老子英雄兒好漢”“兒子英雄爹好漢”等問題。我準備好了有人反駁,結果平安無事。在領導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倡導“兼顧公平”,並作為原則來推行時,我發數篇文章批評領導不應該把公平放在兼顧的地位。在有人為“兼顧公平論”粉飾,講“第一次分配講效率,第二次分配講公平”時,我提出第一次分配、第二次分配都要講公平,甚至在被我稱為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慈善、救濟工作中也要把公平放在首位。到目前為止,尚未見到反批評的文章,以後不知怎樣?
還有一次,我在《社會科學》雜誌上發了篇《馬克思主義多樣化問題》,講不同國家結合本國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,各美其美,各稱自己為“有特色”,這就會產生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流派,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。不久,上面批評“馬克思主義多元化”的說法。我想這次逃不掉了,沒想到《社會科學》編輯部保護了我。他們認為“多樣”不等於“多元”,鄧偉志是講“多樣”,不必列為錯誤。上面也沒追究。這說明理論界是千方百計愛護、保護學者的。
有些爭論是來自於橫向的,那是十分正常的。我是在70年代末第一個替港澳文人曹聚仁說好話的。很多書上講他是“反動文人”。我講他不反動,立即遭到上海一位在40年代與曹聚仁有過爭執的老人反對。老人告我一狀,還說我與曹聚仁的夫人鄧珂雲有親戚才為曹翻案的。領導找我談話時,我說鄧珂雲是廣東人,我是安徽人,我至今沒見過鄧珂雲這位“姑姑”,不過,我正想向“珂雲姑姑”借書,再寫文章為曹聚仁翻案。
80年代初,我在上海《文匯報》連發《家庭的淡化問題》《中國的學派為什麼這麼少》《淡化當官心理——談當官與做學問的函數關係》三篇文章,篇篇引發爭論。有位工程師業務很好,但不會做家務。他妻子是優秀中學教師,教育部請他妻子到北京編教材,這是很光榮的任務。他妻子沒去過北京,很想去北京,但也擔心她一走,家裡的事放心不下。我那《家庭的淡化問題》文章是星期天刊出的。他妻子看後,把報紙往丈夫身上一扔,說:“家庭淡化,我去北京決心定了。”工程師勉強同意。想不到幾天後,工程師一人在家,越來越感到不便,一氣之下寫信向鄧偉志要人,要文匯報“還我妻子”。我那三篇文章在文匯報及其內部刊物《理論探討》上都展開過討論,外地的報刊也發表正能、負能兩類文章。後來這三篇文章被媒體稱作“鄧氏三論”。30多年過去了,現在還有人提起這“三論”。
1979年有家刊物充斥着“耳朵認字”“腋下認字”“舌頭認字”“生殖器認字”的文章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車公庄看了被刊物稱為“之最”的兩姐妹的表演,很明顯是弄虛作假。20年代在周恩來領導下的特科工作、後任外貿部長的李強對我等說:“什麼耳朵認字?這戲法顧順章早就在舞台上表演過。”我公開指出耳朵、腋下認字等是作假,招來一片罵聲。後來我不得已出了本《偽科學批判記》,沒見讀者批評。爭論總有平息的時候。
還有,1985、86年,我應上海人民廣播電台“學習節目”編輯之邀,辦了個“鄧偉志信箱”。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以真名實姓掛牌的節目,聽眾歡迎,領導重視。上海台還在全國會議上介紹了辦“鄧偉志信箱”的經驗。就在電台把這個節目評為優秀節目,即將發獎時,有人向上反映節目有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”。怎麼辦?獎是按程序評的,不發不好,發也不好。電台想了個好辦法:我不出席發獎大會,獎品會後由編輯送我家中,“兩全齊美”,進退自如。
在學術上,我是於1981年2月第一個在社會學重建後在全國第一個社會學系開設“家庭社會學”課程的。我是於1982、83年在國內第一個提倡“婦女學”的。因為我了解國內外的貧困階層貧困到何等地步,便着力提倡民生社會學、貧困社會學、貧困文化學。我連篇累牘地大講社會平衡論、社會張力論、社會矛盾論。在今年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時,我又提出建立一門“改革學”,希望用理論高屋建瓴地指導改革開放的深化。我提出了改革學的“八大規律”:目標守恆律、一改百改律、貧富均衡律、快慢有節律、進出有則律、內外有別律、多樣包容律、上下一心律。

撫今追昔,追惜撫今,深感自己在學術上只不過是飄浮在知識海洋邊上的一葉小舟。
如果說我還有點理論勇氣的話,那是因為70年前,我10歲時親眼看見過解放軍的戰鬥英雄倒在血泊中,那是因為解放軍戰士冒着生命危險把我送出戰場,讓我死裡逃生。我的家鄉是淮海戰場。我見過不怕死的英雄,英雄的精神感染我不怕死。因此在理論上受挫時,我會愈挫愈勇。倒楣時也不是一點都不怕,不太怕是絕對做得到的。我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對付倒楣,以馬列毛的語言頂掉“政治帽子”。一觸即跳不是學者應有的氣度。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,也應當感謝人花氣力吹毛,感謝人家找出了“疵”。天下沒有無疵之佳作,何況我們的拙作!要堵住人家的嘴應在寫作過程中下苦功,堵在文章刊出之前,文章刊出之後就應當歡迎七嘴八舌了。虱多不癢,遇到的爭議多了,我索性寫文章講:我的名字叫鄧偉志,我的號叫“鄧爭議”。做學問不可能沒爭議,爭議是推力,推動邏輯更嚴密,概念更準確。我的理論勇氣還來自於一位1948在我們家鄉的戰場上當記者,1969年是中國駐聯邦德國記者,接着又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的王殊。王殊這個人了不起,在很多國家都認為聯邦德國是軍國主義時,他敢於向中央反映聯邦德國是和平主義,並建議中國與聯邦德國建交。這在當時簡直是“冒天下之大不韙”,甚至可以認為是“認敵為友”。他的建議引起毛主席、周總理的關注和稱讚。1976年10月“四人幫”粉碎當天,耿飈點名要他深夜接管《紅旗》雜誌,任總編輯。76年底38歲的我,借調在《紅旗》雜誌寫批“四人幫”的文章,在他領導下工作。大家一再請他講兩次見毛主席的過程。我們聽後都為他的實事求是、敢於諫言的精神所感動。他這位曾經有一個月平均每天寫3.3篇報道的筆杆子,晚年擔任寫作學會會長,我更認識到寫作需要他那樣的膽量。我即使不能像他那樣“敢為天下先”,咱至少也該做到敢為一座“山下先”。
如果說我還有點學術成果的話,那應當歸功於黨和人民的培養。我讀大學享受全額助學金,另發兩三元補貼。那時的兩三元相當於今天的幾百元。沒有助學金我上不了大學,只會是個泥腿子。我能提出改革學,是因為我聽過1977年出國的四個代表團的報告傳達,是因為北京的按勞分配討論、生產力、生產目的討論,我都沾了點邊,是因為1978年在“真理標準討論”幾天後,我便得風氣之先,較早地聽到中央黨校《理論動態》主編吳江的講解,接觸到支持討論的幾位大人物,是因為我在1978年的科學大會上做一點簡報工作,親耳聽到鄧小平《科學的春天》的講話以及科學家們的發言,是因為我曾在為鄧小平起草《解放思想,團結一致向前看》講話的理論家身邊工作,受到他們特殊的教育和關懷。改革改掉了理論上的舊框框,開放促使學人放開了思想的千里馬。

幾十年來,我是在出錯與糾錯中匍匐前進的,是從不錯被誤為大錯、又被好人保護過關,側身擠過來的。人們常講酸甜苦辣,我從自己的經歷上覺得這四個字描繪得不全,我又加了四個字“咸癢澀麻”。我是酸甜苦辣、咸癢澀麻“人生八味”都嘗過。不過,這比之於許多國家有成就的學者所遇到的挫折是微不足道的。馬克思因為有超人的高見遭受關押、驅逐。王羲之說:“仰觀宇宙之大,俯察品類之盛,所以遊目騁懷。”讀和走都是“游目”,我相信“游”過“目”的人,胸懷會豁達的,會尊重差異,包容多樣的。
作為學者寧為學問所困,不為財富所累。學術機構的門上對聯應當是:“追求發財莫進來,要想當官走別路。”為了學問,我的做法是:生活簡單化,知識複雜化。多灌腦袋,少管口袋。在吃的方面,我認為價格高的不一定營養好,營養好的不一定對我好,營養講平衡。我的體重長期保持在七十二三公斤,可能與我不講究吃喝有直接關係。過去美國有位華人諾獎獲得者丁肇中,他的團隊進了實驗室,七天七夜不得出來。吃住得服從科學實驗。想想看,實驗室的生活再好能好到哪裡?以色列請愛因斯坦去當總統,他不去,發人深思。天才就是汗水。學人要把汗水曬在學問上。
灑汗水的過程是:“讀+走”→寫,在寫的時候,在寫了遇到別人跟你商榷的時候,又會感到走得不多,讀得太少,於是再來個“再讀+再走”→再寫,循環往複,以至無窮,螺旋式上升。